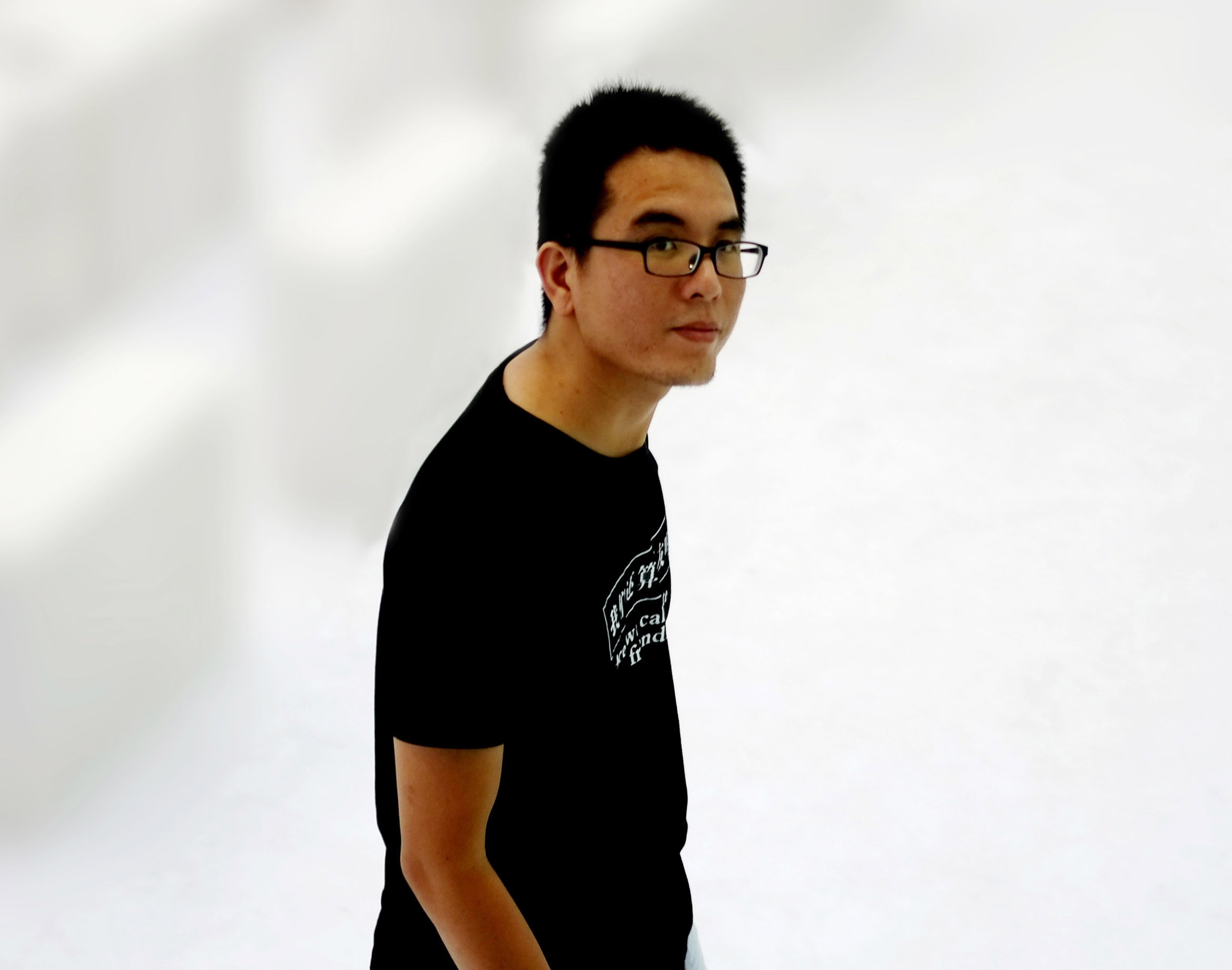崔广宇
简历
1974年出生于台北,1997年国立台北艺术大学毕业。崔广宇在台湾算是「新世代艺术家」,可说是目前国内当代艺坛上相当活跃及备受国际瞩目的新秀,作品《系统生活捷径―表皮生活圈系列》、《十八铜人,穿透系列》等皆在国际性的大展,如「〈2004台北双年展〉、〈第51届威尼斯双年展〉中展出过,并广受好评。他以录影形式结合行为艺术,成为少数能够做出具有「观念艺术」内涵的杰出创作者。作品亦曾受邀至英国、日本、韩国、德国、西班牙等地展出。
1996年起,崔广宇所参与的艺术团体「后八」于台湾的都会社区中进行一连串的丈量、测试与拟态的行动艺术创作。其后的个人创作亦沿着此一路线,主要以城市空间为舞台,透过自己的身体与生活环境之间的接触、互动、介入等行为,探刺我们日常活环境的宽容度。代表的作品有《十八铜人,穿透 穿透性》(2001)、《系统生活捷径—表皮生活圈》系列(2002)、《我很好,我并没有淋溼》(2002)、《城市精神》(2004)等。
在《十八铜人―穿透系列》中,艺术家用自己的头去撞击公共空间中的牆、凋塑物、车箱、路树、牛隻等物体。看似荒谬、愚蠢、无聊的行为,其实充满了对于生活环境的各种指涉及隐喻。身体的撞击行为代表了主体与环境之间的对抗与矛盾;想要穿透的意欲,却遭到物体物理性上无法穿透的无情反击,暗喻人在现实社会中与各种制约与体制不断冲撞的处境。
综观崔广宇的创作,他以身体为媒介,使用「表皮」、「捷径」和「穿透」等字眼伴随肢体的动作及富含社会性、游戏性的演出,实际上是意图揭露我们日常生活底层下的某种真相。艺评人黄海鸣指出:「崔广宇的表演录像作品除了散发立即的吸引力,其中不断重複及变化的元素,看似无厘头、搞笑、愚蠢,但却又能触动人深刻或许还是沉重的反思。」(刘建国)
艺术家作品


站在感性的前端——走在快捷方式上的崔广宇
文/汤皇珍
崔广宇,1974年生,艺术学院毕业。曾经出没于关渡平原每季稻草燃烟时分,曾经以身撞物,听说试图穿入汽车、树木以及大象当中。
快捷方式往往是直接的,像是可以快速到达或方便取用,快捷方式有时也是一种激化的非常手段,崔广宇说:我以一种像是快捷方式的方法与环境对抗。他的作品由对应环境开始。以身试物,直接的叫人心惊,亦是叫人不得不回首瞻望。
崔广宇把自己的发表称为行动记录。1995年起,还是学生的他将系上呈长条型的画廊围堵起来,灌入水放上木板,他在这些木板上来回穿行直到浮在水上的木板因为一次次的位移而终致无法再由这块木板联系到那块木板,穿行的人于是掉入水中。接着,他与同学制作了一双简陋的弹簧鞋跌跌撞撞由学校所在的关渡开始出发,前去绕行当时自己经常往来的空间。看看穿上弹簧鞋后环境是不是有所改变?无效益的行为,可笑又很疯狂。细想后更有苍凉--似乎看见人在环境中因为某种条件不得不然的反应,失望与希望的挣扎。似游戏又似笑话,这样认真的荒唐。
接着是崔广宇服役之前的三件作品:模仿、代步以及天降甘霖。每一件又都是活生生的把自己暴露于行为看似失常可笑的状态。「模仿」是竭尽所能把人仿真为物。要知道人类肢体全力想变成一棵树、一种风动的不可能与严肃,对应在树的旁边。「代步」则是坐于附有滑轮的椅子上从斜坡反复滑溜而下,看似失速般危险也像游戏般漫不经心,像是逃离又像很认真的在代步。「从天而降」,降的不是沙漠旅人需要的甘霖,而是些会打死人的大型家俱对象。崔广宇在这样的「枪林弹雨」间闪躲,没有砸中目标的对象应声摔毁,但也可能应声昏倒的是作者。然而若是果真我们的确身处在如此一个时时天降「甘霖」的环境,受伤的便可能是人了!这个认真的笑话是十足辛辣。因为用的是真实的生命、微小的人。
什么样的危机让我们如此致命的闪躲?崔广宇以身试物的行径是不是在让我们笑出眼泪时,我们才得幡然了悟此间的失常行径是意有所指。这个快捷方式可以快速到达或方便取用人的失常。直指着环境中的不合理。不合理的所在是不是真有异物从天而降?从天而降的异物是什么?有形的物?或是意识型态上可能的阻隔与无感?像一场寓言的重现,当异物已经占满领空,是不是只有被迫环境中的人一再以一种强烈不属于人类本能的行径来应对?一再强迫我们看见对应者的失常以及危机?我们要如何透过这一次又一次随即消失却可能致命的行动,在艺术家有意识的执行中来思考艺术在意识型态上能够引爆的触接?在呕吐后得以重生?
18铜人系列是崔广宇的近作,就像受证加持,通过考验者得以铜身进入化境。对环境产生抗体。这些考验目前有穿透性、感受性、自发性;分别是以身撞物,试图穿透;以身受物,试图明白由身后丢来的东西是什么,以及随时呕吐直到达成见物就吐的自发性。
很堂皇,很荒谬,又再次置身于与本能相反的危机之中,但人人希望成为18铜身,得以不再对环境有所畏惧。崔广宇说:不要担心,我还活着。这样的看似天真执着,这样的毫无退缩,这样的荒旦不稽却又苍凉,我们的环境究竟怎么了,让生活于其中的人必须如此对应?
甚至没有时间明白作品发生了什么?当我们以身行进,甚至致命时会不会引来一点注目?如果生命中的努力适应不良都不值得一顾,那么我宁可选择就做一个失常的人,而不是一切无动于心的圣人或是放逐的羊。
站在感性的前端,维持艺术的脆弱与独一无二。
第六届台新奖揭晓:崔广宇获视觉艺术奖
举办已臻六届的台新艺术奖,随着声誉与影响力逐渐扩大,今年首次在美术馆举办入围展,并于台新金控总部圆厅举行颁奖典礼。典礼在犹如「施工中」的后现代舞台以及另类的打击乐表演中开场,两位打扮成MIB的主持人,分别为剧场导演李建常以及获得视觉艺术类入围的艺术家苏汇宇,两人诙谐的对白为颁奖现场带来一派轻松、幽默的青春气息,正反映了趋向成熟的台新艺术奖,定调为鼓励年轻创作者激发创意的走向。而此次百万大奖得主,果然清一色为六年级生:以「系统生活快捷方式:城市瞎摸」入围的崔广宇,摘下了视觉艺术类大奖;表演艺术类得主,则是成军不久以《速度》入围的「骉舞剧场」;「莎士比亚的妹妹们的剧团」以作品《残,。》,获得了「评审团特别奖」。
「花了六年两个奖都收集到了」,在第一届就拿到「评审团特别奖」的崔广宇,再次从台新奖推手林曼丽手中接过「视觉艺术大奖」。决审团以「超常的机敏和幽默感介入城市文化的测量与批判,利用现有的资源借力使力,呈现出都市成规与生活型态之矛盾,充分展现了一种诗性的荒谬感……」为主由,在几乎没有异议之下,将大奖颁给崔广宇。
自大学时代创作以来,崔广宇在作品中传达出清晰的个人思维,并拥有一定的创作持续力与大展资历,决审团主席黄海鸣指出,艺术家的「创作脉络」正是获奖的重要判准,这在过去几届的台新奖得主,梅丁衍、汤皇珍等人身上,都可以得到印证。来自卢森堡大公美术馆的策展人暨文化部总监克莱蒙.明尼格悌(Clément Minighetti)说,第一次看崔广宇的作品即深受吸引:在崔广宇录像作品中,许多行径都像是一个「傻子」,但他敏锐地点出台湾文化甚或是异国文化(例如其于利物浦、荷兰进行的创作计划)中某种真实的面貌。尤其可贵的是,崔广宇的立场坚定,知道如何用艺术去介入不同的文化,在戏谑、玩笑中提出他的观察,并且能够与全球化的世界相呼应,唤起不同地区与文化背景的观众共鸣。另一位决审上海张江当代艺术馆馆长李旭则认为,从崔广宇目前思想的成熟度和作品的完成度来看,是颁给此奖的最佳时机,错过了可能就不再适合。其他入围者还年轻,未来还有被提名的机会。
此届在表演艺术方面,爆出了黑马。获大奖的「骉舞剧场」,由一群异于传统的年轻男舞者所组成,虽然仅仅创立三年,但在肢体语言上的展现令人惊艳,利用概念式而非叙述式的尝试,发展出独特的舞蹈语汇。此作的获奖,对于台湾表演艺术界创作上的世代断层,别具特殊意义。相较于视觉艺术青睐于作品发展成熟,在国际展演甚至艺术市场均有成就的创作者,表演艺术决审团的给奖共识,却在于鼓励「创新」的层面,刻意跳过已具备清楚定义的团体,着重尚在发展中、甚至不知道如何命名的艺术表现。两类评审对于给奖,显然呈现了不同的思考逻辑与美学意趣,大奖的决定性判准,最终仍落在作品的个别考虑以及决审的共识上。
是不是一件「艺术作品」?
台新银行文化艺术基金会董事长吴东亮表示,为了落实「入围就是肯定」,基金会将会提供所有入围艺术家未来的国际邀约与展演协助。而这次远道邀请多位国际评审,对于本届台新艺术奖在决审过程增加的艺术家面谈沟通,都表示十分肯定,更因此了解台湾当代艺术的面貌。来自巴黎克泰尔艺术中心的表演艺术决审吉尔.布卡(Gilles Bouckaert)提到,许多作品涉及传统文化,在短时间中仅凭评审单一方面的理解,有其困难性。但在与艺术家面对面时,藉由更深入的询问,对作品的内涵与艺术家的想法能有更深的掌握。
其他视觉艺术未获奖的作品,评审认为,郭奕臣的《突变》在创作技术上纯熟并具有魅力,但试图表达过多的面向,以致于每一个主题无法被完整的发展,作品力道反而因此减弱;至于苏汇宇商业广告式的《枪下非亡魂》,明尼格悌觉得虽是件不错的作品,但作品少了一些东西,没有崔广宇的作品来得吸引人。
也许是因为中国与台湾不同的文化脉络,李旭对于以长时间考据、严谨精心拍摄,最后以情境戏剧的方式,呈现台湾现当代艺术史脉络的《以艺术之名》,表示特别赞赏,然而「何以此类型作品能入围?」则让决审们辩论许久。《以艺术之名》毕竟是一件「团体合作」,而非具有艺术家个人观点的作品,在台湾已有过先例,李旭不讳言自己最后因此改变初衷,而转投崔广宇。抱持同样观点的明尼格悌,虽肯定《以艺术之名》推广台湾当代艺术的努力,但认其终究只能说是一系列的纪录片,而不是一件「艺术作品」。
类似的争议,亦发生在许秀云的《希望之海》壁画,此作为表演艺术决审团共同推选出的「评审团特别奖」。表演艺术决审香港艺术节总监梁掌玮说,此作加入了当地学生与民众的参与,藉由艺术创作让更多人正视地方工业污染的问题,进而扩大讨论,在香港很少看见,借着艺术家一人之力去促成一个集体的艺术行动,令人感动。然而,视觉艺术类评审则认为,以艺术的角度来看,这类作品并不特殊,也不算创新。明尼格悌直言,若单看最后的《希望之海》壁画,他并不认为这是一件艺术作品。
提供社会改变的力量?
台新奖经过一年的提名程序与重重筛选的关卡,最后入围的作品可说是反映了整体评审们的集体意志与审美标准。从公共电视《以艺术之名》以及许秀云《希望之海》的入围,即凸显了台湾艺术界存在着期许台湾创作者「社会关怀」理想的价值共识。这甚至更激进地反映在是否要将发起保留乐生疗养院文化行动的「乐生青年联盟」纳入视觉艺术入围作品的争议上。但考虑台新奖规定获奖人必须是艺术家或立案团体,而乐生青年联盟的出发点是一个自发性的社会行动,既非一个艺术作品也非展览,因而作罢。
与此相较,决审对于「是否是一件艺术作品」,则倾向于美术馆、画廊展出的传统纯艺术定义,虽然符合普遍对于艺术作品的看法,却可能排除了在形式与表现另类、挑战艺术定义的作品。吴玛悧认为,虽然台新奖最终还是以肯定一位表现突出的艺术家为主,但仍须关注台湾艺术整体发展的现况;如何去体会不同类型作品中的创作精髓,是台新奖日后可以努力的目标。
此外,本届视觉艺术类决审由历年的五位减为三位,在多元观点的平衡上有显不足,无法达成充分而全面的讨论,黄海鸣认为五位仍是较适合的配置。蒋伯欣亦建议,在评委的组成上也应维持某种异质性,避免同构型过高的评审参与,或者增加提名委员在各地的数量与分散程度,在评选过程中便能保有更多元异质的声音,如此不受当代艺术主流认可的底层、边陲,才有发声的机会。
从创始迄今六年以来,台新奖的操作机制愈发纯熟后,是否仍能汇集台湾艺术社群的能量,提供社会朝向某个方向的改变力量?或者渐渐定型成为「某些类型创作」的推手?台新艺术奖的定位是什么,是否要支持在精神上带有社会指标性的事件?对于这些艺术在社会中扮演的角色,艺术的终极价值的基本思考,仍然是每年辩证入围与给奖判准时不断面对的命题。抑或者,当一个民间企业奖项在设计严密完整的提名程序,不断完备化各项推广机制,搭建艺术社群的交流讨论平台之后,对于这样不断质问与反思的开放性问题,即将此重任交付给每一届真正参与提名与评审者来决定了。